说说“洗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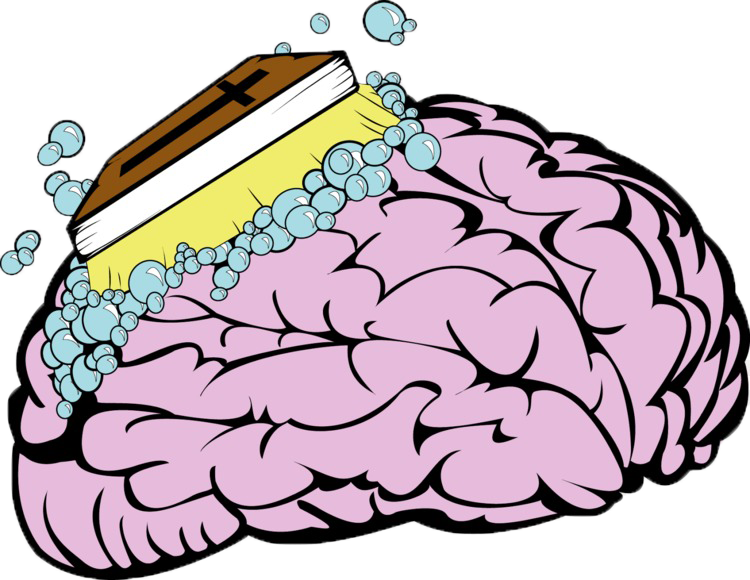
洗脑这个词,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听说了,童年的我还不擅长抽象想象,于是根据字面意思把洗脑理解成一个物理动作。
在我的想象中,我认为这应当是一种和医学手术类似的东西,手术者给被手术者脑袋里面灌入一些清洁剂、消毒剂一类的东西,然后用某种类似水龙头一样的东西冲洗后者的脑花,以达到清洗和消毒的作用。后来我又听大人说,一个人被洗脑之后,就会相信一些原来不相信的莫名其妙的东西,进而六亲不认,胡作非为,于是在我的构想里面,这个过程又多了一些更为高深的步骤,那就是洗脑前需要灌入的那些不明液体,它们应当是承载了一些神奇的物质的,通过这些神奇的物质,我们可以让被洗的人相信一些本来不信的东西,做一些本来不会做的事情。
有趣的是大人们都在讨论被传销洗脑前后的那些人们所干的事情,却从不说“洗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又一向不愿意掺和进大人们的讨论,于是对于洗脑这个词的上述想象,一直就那么停留在我整个童年的记忆里,以至于至今仍然记得。
讲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说明童年的我是一个脑袋糊里糊涂的笨小孩,恰恰相反,童年的我在大人们的圈子里以相以聪明、记忆力好闻名,背个古诗古文,一直是那时期我们家的传统保留节目。当然我说这个故事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证明童年的自己想象力多么的丰富,我只是想说,聪明的人总是过分相信自己的理解和推理能力,而忽略了沟通的重要性。
拿洗脑这个例子来说,我并没有查询过开颅手术目前能做到些什么效果,也不知道当时咱们对脑花的研究到了何种地步,是否有能力精确的对某块脑花做一些操作之类。当然,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子不应该懂得这些,甚至他都不应该知道大脑里面是什么东西,但是坏就坏在我比其他小孩还是多了那么一点知识体系——那会我们镇上和我同龄的小孩,有的连汉语常用字、加减乘除都没整明白,相对于他们,早早就读完了十万个为什么的我,当然会有一种优越感,后来我发现很多人的优越感和那个时期的我自己极为类似,那就是坚定的认为——这个东西我知道原理,剩下的就是一些操作的细节而已。
那会的我知道,人的脑袋里面是像核桃一样的脑花,算算术、背古诗都靠这脑花去运行,我比其他人多的这点可怜的知识,助长了我自己的一种嚣张气焰,认为天下事都不过是在之前这个框架里面去添加细节而已,于是当我听说“洗脑”这个词汇的时候,这种优越感和一点点比别人多的知识体系,直接促使了我放弃和他人沟通,选择自己脑补,这就有了上面那个笑话。
洗脑当然不是我小时候所理解的那个意思,这个故事本来是一个平凡的童年笑话,我却始终记得它,因为这个故事虽然可笑,但是里面的教训我们却总是在犯。
我后来读到不少和我类似的打脸案例,比如19世纪末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迈克尔逊先生,在他的演讲中宣称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以后只需要简单的的修修补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知道他肯定是犯了和我童年一样的错误,果不其然,在他口中所说的“两朵不起眼的乌云”,后来几乎推翻了整个经典物理学的大厦,闹得物理学界人仰马翻。
还有满清末年时期,官僚们对于外来的这些洋人总是一种俯视的心态,认为其不过是“奇工淫技”突出而已,若论“人心之学”,还是得靠我中华学术,换言之这种理论就认为,西洋的那些科技,只是用来补充我们伟大渊深的“人心之学”的,是偏门和末道,要论正学,还是靠我们这一套。
由此我发现一个规律,简单说来就是:“当你认为你已经手握了真理的时候,正是你开始变蠢的时候。”
这句话和大物理学家波尔评价量子力学那句名言类似,他说如果一个人不为量子力学感到困惑,那只能说明他并没有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自然科学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因为实验结果总是冷冰冰的摆在那里,科学家们没有别的路子干掉实验结果,只能想尽办法完善自己的理论,这就有了科学的进步。
社会科学则不然,有些东西我们辩论了这么久,吵吵嚷嚷的我看也没得出一个什么靠谱的结论,但就是这些半成品的结论,持有他们的人的信心却总是比19世纪的物理学家们还要充足,后者还出于谨慎的说了一句“我们还有两朵乌云”,而前者却总是迫不及待要把自己的发现塞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还是拿“洗脑”这个词来举例,现在互联网上出现一个神奇的现象,那就是大家都喜欢说别人“被洗了脑”,这个问题总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基于人所皆知的事实,“洗脑”绝不是我童年所理解的那样的一种外科手术,可以通过疤痕、手术记录单来判断这一行为在过去的发生与否,没有这样显而易见的证据,我们推断一个人有没有被洗脑,其实是充满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的,换言之,这个断定并不是那么好下,但是我所见的声称另一方被洗了脑的人,在给出这样的判断之后,并没有丝毫要证明的意思,他们马上就会迅速聚在一起,说着一些不太能看懂的东西,然后获得一种集体嘲笑他人的快感,似乎洗脑这个判断,并不是为了严谨的确认某个对象脑袋的状况,而只是他们接头的一个暗号——声称某个人物、某种言论是被洗脑了,这种声明就像是昆虫发出的信息素,立马可以聚集一大批同类,大家聚在一起继续散发信息素,相互愉悦着,像萤火虫聚在一起发光。
如果我们严谨一点,就可以知道,给出任何判断,一定要有事实依据,而不是人数上的依据。波尔做物理学研究的时候,从来不会根据某篇论文的跟帖数量来判断对错与否,而只是相信实验。与此同理,我们每个人都不如说是生活在一个社会科学的大实验室里面,在研究一些别人的关于社会科学的言论的时候,我看也可以效仿一下物理学家们的态度,那就是不要把话说太死,毕竟一百年前说的东西,过了一百年还被后人拉出来嘲笑,其实是一件不太好受的事情,就好比我现在提到童年时莫名其妙的关于“洗脑”的想象,还是会觉得害臊,羞愧于自己当初胸有成竹的当了那么多年的傻逼。